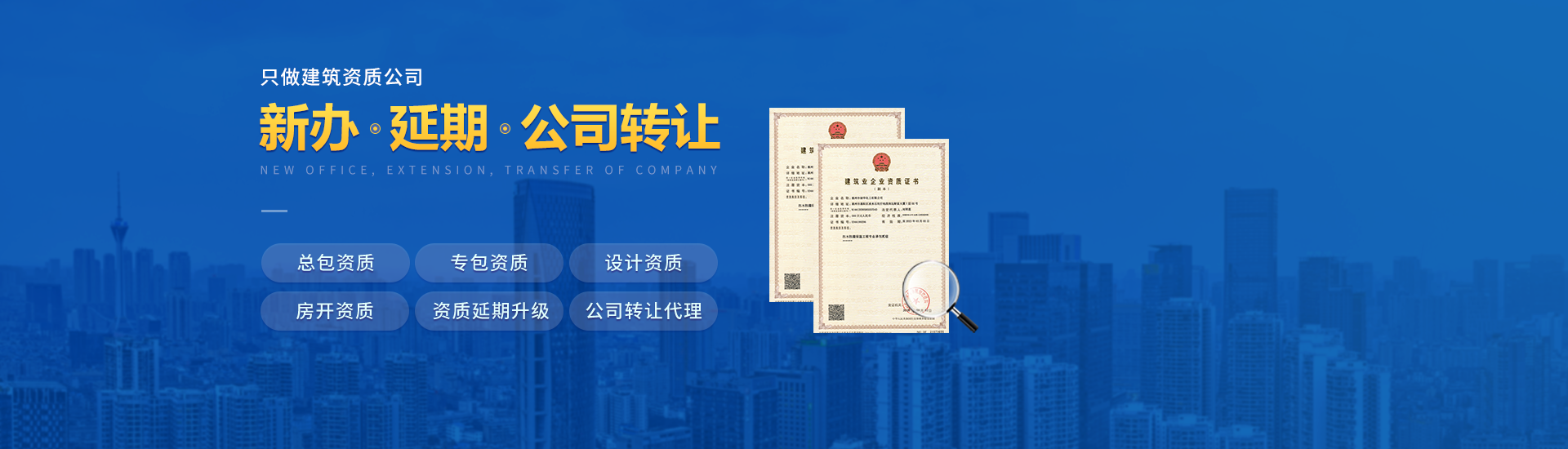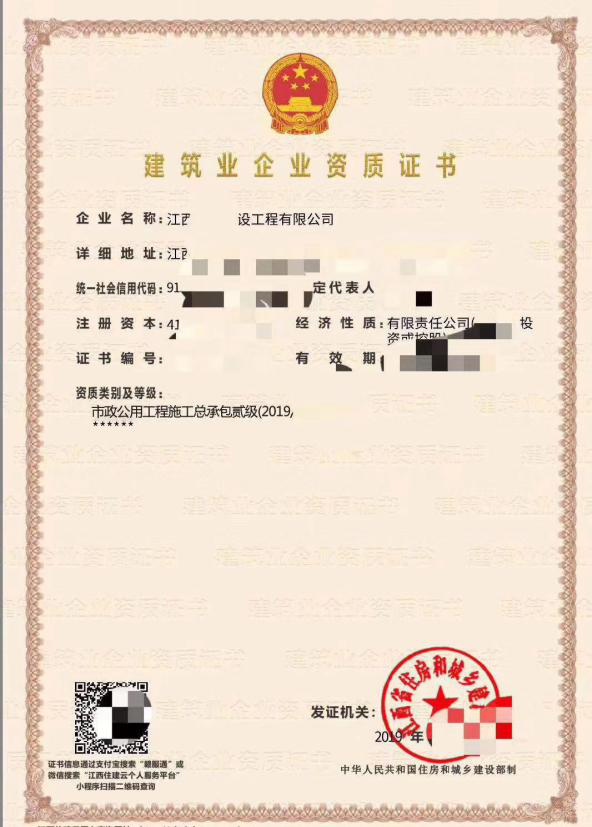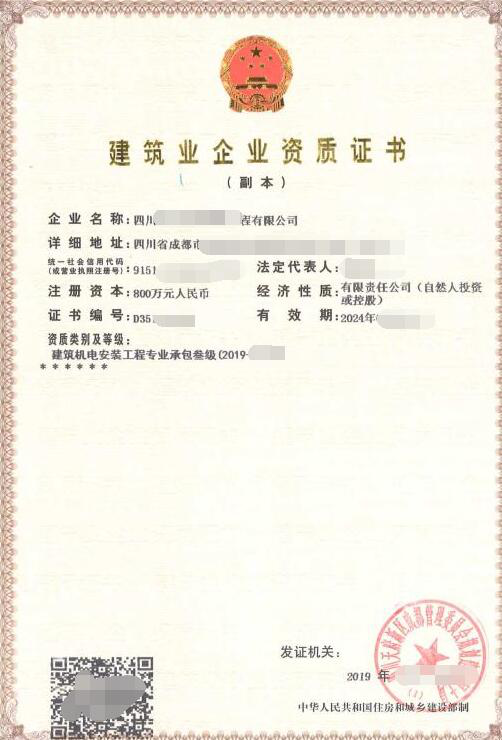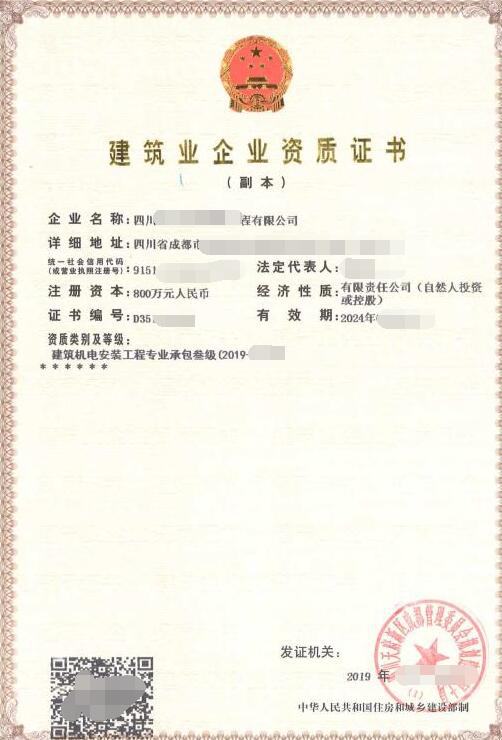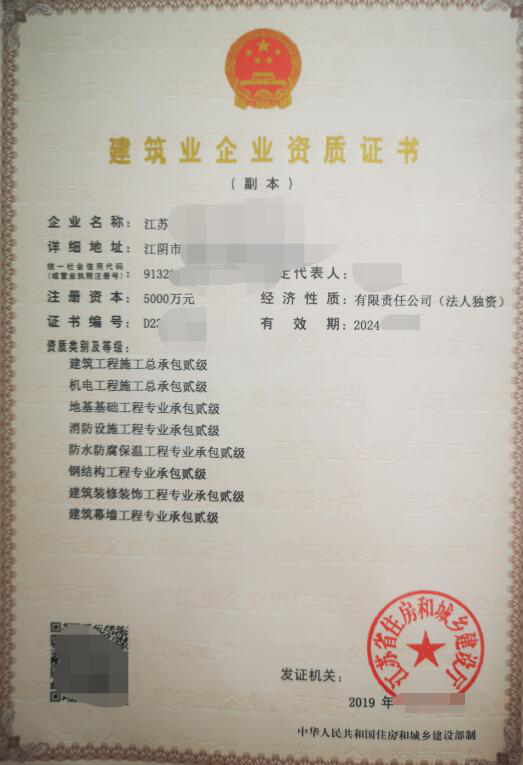以藝術為橋,讓村民變身“文化創客”;以“非遺”為魂,讓千年技藝重煥生機;以建筑為核,讓古老智慧融入當代生活……傳統村落是民俗文化的鮮活載體,承載著鄉愁記憶與文明密碼。如何讓傳統村落中的老屋不褪色、文脈不斷流?從浙南古村的藝術共創,到太行深處的瓷韻新生,再到雨林秘境的船屋守望,經過各地住房城鄉建設等部門的大力推動,傳統村落在保護原始風貌的基礎上創新活化路徑,在文化賦能中實現“活態傳承”,成為鄉愁所系、文明所依的精神家園。
藝術扎根鄉土村 落變身“活態美術館”
浙江省麗水市松陽縣的驕陽難擋八方來客的熱情。錯落分布的老屋、幽靜深邃的石板巷與秀美的自然風光交織,讓游客沉浸其中。作為華東地區古村落數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區域,松陽縣在當地住房城鄉建設等部門指導下,不少淪為危房的建筑得到有效保護,令傳統村落煥發出新的活力,散發著濃郁的文化氣息。
在三都鄉松莊村,“未織之境”主題展匯聚了國內外藝術家與村民共創的藝術作品,吸引了一撥又一撥游客駐足。村民徐家美指著展品打趣地說:“這是我編的竹籃,好多人都很感興趣,我是不是算半個藝術家了?”
擁有600余年歷史的松莊村是傳統村落保護的“受益者”。通過系統修繕古民居、古橋、古道,村莊原始風貌與歷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為更好地實現發展,同時避免同質化,當地選擇藝術賦能,走特色發展之路——建設名為“織”的現代美術館便是其中一步。為打消村民疑慮,三都鄉政府依托“三鄉人(原鄉人、歸鄉人、新鄉人)共富協商機制”,多次組織村民與業主代表議事,詳細解讀設計理念、建設規劃并逐戶溝通,最終贏得支持。
美術館落地后,村民的視野隨之被打開了。老屋墻面的涂鴉靈感源自村莊日常;“山民劇場”里,音樂會、話劇、戲曲輪番上演;巷弄間,形態各異的藝術作品點綴其中。更可貴的是,人們紛紛主動參與藝術創作。藝術家與村民共創的作品被轉化為明信片、冰箱貼等文創產品,銷往各地。
藝術價值的轉化帶動了村集體收入的顯著增長:松莊村的游客量年均增長超20%,2024年文旅收入突破500萬元。今年舉辦的“藝術共創分享會”上,參與文創設計的村民還得到了設計分紅。而該村的實踐也已成為松陽縣傳統村落活態傳承的典型——通過創新實施“藝術家入駐鄉村計劃”,當地已經建成多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吸引大量藝術家、文創客扎根鄉村,讓村民成為文化賦能的參與者和受益者。
千年窯火重燃 古村承載“瓷都記憶”
石頭路蜿蜒,匣缽墻斑駁,古窯遺址靜靜矗立。依山帶水的河北省石家莊市井陘縣南橫口村,這座藏于太行深處的中國傳統村落承載著河北四大名窯之一井陘窯的千年記憶,今天正以文化保護與創新利用并重的方式,讓千年瓷韻煥發新生。
南橫口村的制瓷歷史可追溯至隋代,歷經1400余年燒造歲月,其“戳印填彩”等裝飾工藝獨具特色。但因地處大山深處,南橫口村深陷“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困境。“交通閉塞,排水、照明都跟不上,再好的瓷文化也引不來人。”在村里生活30多年的梁淑芳回憶道。近年來,當地在相關部門支持下,整合資金修繕基礎設施,錨定陶瓷文化內核,啟動系統性保護利用:建起井陘窯博物館,展出百余件歷代古瓷;成立研究中心,邀請老匠人傳藝授徒;將燒制瓷器廢棄的匣缽砌成特色墻體,讓工業遺存變身為獨特地標。
千年窯火未熄,古村煥發新生。如今,這些富有特色的文化資源為南橫口村發展提供了“動能”:村中半數以上村民掌握制瓷手藝,他們在商店現場展演“戳印填彩”技藝,讓游客能親手觸摸陶土,體驗拉坯樂趣;網紅咖啡店里,店主與老人閑話村史,陶瓷文創與鄉土故事在此交融;民宿、手作店等新業態次第涌現,與古窯遺址、匣缽墻構成“露天瓷器博物館”,讓游客步步賞美景、處處有故事。
“我們以前暑假經常去海邊兒,現在發現深山里的傳統村落更有文化味兒,所以帶著孩子來看看,還能學不少知識。”一位來自天津的游客表示。從深山窯址到文化地標,南橫口村以“保護+傳承+創新”的路徑,讓千年陶瓷文化在當代生活中延續文脈、綻放新韻。
守護船型老屋 黎族智慧在雨林延續
海南島西部的雨林深處,白查村的夏日空氣里浮動著茅草特有的清香。黎族船型屋營造技藝傳承人符打因正帶領村民在屋頂勞作,靈巧的雙手上下翻飛,將一捆捆自山間采來的茅草用藤條固定。“這次用于修繕的材料全是附近山上現采的,下個月就能完工。”他抹去額頭的汗珠,望向錯落分布的船型屋群。這些形似倒扣木船的茅草屋,在此已守望了數百年光陰。 作為海南現存規模最大的黎族傳統聚落,白查村現存的87間船型屋是獨特的“招牌”——厚實的茅草屋頂幾乎垂至地面,勾勒出獨特的船篷輪廓。走進屋內,3根高柱與6根矮柱撐起整個空間。“這叫‘三柱六椽’構造。”東方市博物館館長秦巍輕撫斑駁的木柱解釋稱,這種凝聚古人智慧的建筑無需鐵釘,全憑白藤捆扎:格木為骨,麻竹作梁,稻草混合泥土敷成墻體,所有材料皆就地取材。
同時作為中國傳統村落,白查村還是黎族文化傳播的重要點位。距離船型屋群不遠處的白查驛站里,民宿客房、黎族餐廳、手工藝展銷館一應俱全。當地文旅企業采用“屋外開發、屋內研學”的運營模式,既保留老屋原始風貌,又讓藤編、黎陶等“非遺”技藝重獲生機。
但很多人不知,這個村落的保護歷程充滿挑戰。2009年村民遷入新村磚瓦房后,空置的老屋在風雨中加速損毀。“茅草頂四年就要換新,無人居住的房屋破損更快。”符打因回憶道。更嚴峻的是技藝傳承危機,2012年,全村僅剩4位掌握營造技藝的老師傅。
為搶救瀕危技藝,在有關部門支持下,東方市連續5年舉辦傳承人培訓班,隊伍已從最初的4人發展至23人。年輕學員跟隨師傅進山選材,學習將茅草捶軟后編織成3平方米的草片。“鋪屋頂最考驗技術,180多片草要按S形交疊鋪設。”新晉傳承人符茂擦著汗笑道。
站在村口高地遠眺,修繕一新的船型屋群與雨林相映成趣。村里建起的研學基地還由傳承人輪流擔任導游,黎族姑娘在船型屋前跳起竹竿舞,生動活潑地展示著黎族文化,來往游人紛紛拍手稱贊。